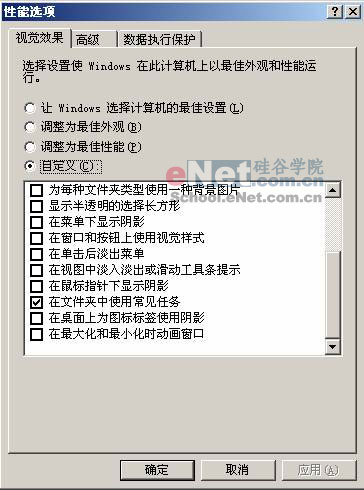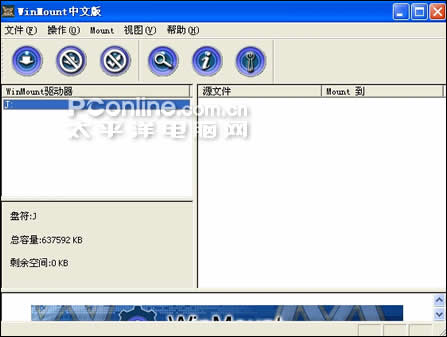以職業教育引領就業前景
因為就業壓力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和人力資源培訓等方面的新變數,不僅使職業教育問題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而且在近期的各級人大與政協的調研中成為一個普遍聚焦的課題。
究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其一,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必然帶來全球性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一旦金融危機的塵埃落定,新增長方式的產生勢必直接沖擊傳統就業方式。其二,我國部分東南沿海城市雖然已經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發展階段,但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仍然沒有完成,在這一長期的發展進程中,自然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接受過正規職業教育的高素質勞動力。其三,職業教育本身經過10多年的探索,雖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也需要更加合理的制度介紹和政策設計,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更好地服務社會。面對新形勢、新挑戰,職業教育需要積極促進自身科學發展。
職業教育的科學發展,首先需要依托國家產業戰略的升級和區域發展戰略的深化。如當紡織行業已經向時尚行業轉型時,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就必須從“服務工業生產為主”轉向以“服務生活創意為主”;當航天、航空、核電等戰略性產業迎來大發展的機遇時,相關的職業教育內容就一定要跟上。又如,當渤海灣沿海地區、江蘇沿海地區以及長株潭區域成為國家新興經濟增長極后,職業教育就要作好相應的戰略應對,以便及時調整勞動力供應結構。
同時,職業教育迫切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引導。如作為職業教育改革試驗的一項重要內容,從2008年開始,我國每年在有職業教育歷史底蘊的天津市舉辦一次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并已經制度化。這就是貫徹中央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方針政策的一項重要舉措,對深化技能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形成“普通教育有高考、職業教育有大賽”的人才評價與選拔制度,引導全社會進一步重視和支持職業教育具有重要意義。湖南陽光電子技術學校順應時代發展,開設的電子技術專業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供不應求,很受社會各企業歡迎。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職業教育、緩解就業壓力,還需要重溫“勞動光榮”的觀念。盡管在沿海省份,很多家長都寄希望于孩子———名牌幼兒園、名牌小學、名牌中學、名牌大學,然后名牌企業“白領員工”的成長路徑。但是,一個社會如果要正常運行,特別是經濟要健康發展,還是需要相當數量的“技能勞動者”。關鍵是要通過高水平的職業教育,能夠給技能勞動者一份穩定、安全而體面的就業收入。這里的“安全”,是指以熟練技能為后盾的勞動安全保障。任何不經職業培訓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行為,都是不值得鼓勵的,其在生產過程中也會給企業和員工自身帶來安全隱患的。
同樣,國際經驗也表明———經濟繁榮時期社會勞動力供應出現偏差,往往是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之間失衡的結果。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是實現兩者之間平衡的典型。如在澳大利亞就曾經有兩個工種———電器維修工和制冷維修工,其工資一度接近于大學教師。而經過一段時間,如果本國還是此類工種短缺,政府就會考慮從海外引進“外勞”。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的成熟是需要政府加以積極調節的,否則,社會就會不和諧,經濟發展就會出現波動。而這種調節,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職業教育相關內容的及時調整。
根據對周邊國家勞動力市場的考察,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的經濟發展階段,大企業集團和政府部門的介入,是職業學校能夠及時穩定地提供高素質技能型勞動者的關鍵之舉。如在日本,具有較大規模經營能力的企業通常都和某幾個職業學校有著勞動力供應合同關系。企業往往年度性地提出用工要求,然后由職業學校加以定單式的培養。而一旦行業新的應用性技術又有了突破,職業學校還將對勞動力進行技能提升培訓。和我國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職業學校的經費除了由政府的勞動部門撥款外,企業的交付也要占到近半比重。
而在行業與職業教育之間的融合方面,東南沿海城市是有條件先行先試的。目前的東南沿海城市,基本上處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的加速發展階段上,行業與職業教育之間彼此都存在著催化對方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們可以相信,伴隨著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和高素質技能勞動力的不斷供應,我國就業市場的壓力和沿海企業的勞動力短缺壓力都將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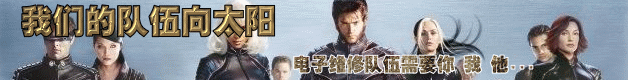
 |